询盘
在过去30天内,用户已发布 0 个询盘需求
发布询盘发布询盘



询盘
在过去30天内,用户已发布 0 个询盘需求
询盘大厅 HOT
每月汇聚全球1.4w+询盘,高效获取商机
货代圈 HOT
为货代销售,提供微信QQ全网商机,拓展合作机会
找代理 HOT
1.1w+全球货代企业聚集,3分钟智能推荐满足您的需求
全球会议
物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端会议之一
交洽会 HOT
博览会
行业活动

迪拜·阿联酋
2025-06

上海·中国
2025-10
金融支付
高效安全的结算服务,一年节省上万元手续费
货运险
普货费率0.02%起,最低保费15元;在线投保,秒出单
货代责任险
保障货代公司经营风险,提供免费法律咨询
船期
覆盖全球主流航线,主流船司,随时随地想查就查
全链路跟踪
打通所有国际海运节点链路,实现跨国集装箱跟踪数字化,可视化体系
AMS
提供资质完备SCAC code,告别繁琐认证和跟踪
ISF
支持ISF5+2和ISF10+2申报,提供Filer code
ACL
提供 Bonded 8000 CODE 回执快速,推送及时
AFR
一站式完成日本海关进境舱单预申报
上海预配
上海口岸预配舱单申报,支持主流船司、船代,回执迅速,价格优惠!
青岛预配
青岛口岸预配舱单,一键导入场站数据!覆盖全船司,全船代,支持日照舱单!
深圳预配
深圳预配+报关,在线跟踪,一键委托
南沙预配
南沙预配+报关,在线跟踪,一键委托
在线报关
支持全国主流口岸报关,AEO高认报关行为您报价护航,报关从未如此简单!
FMC资质服务
FMC在手,美线无忧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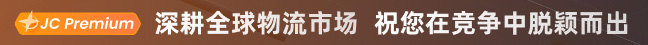





南京港
-
勒阿弗尔

天津新港
-
加里宁格勒

南沙港
-
西哈努克



上海浦东国际机场
-
悉尼机场

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
-
丹尼尔·奥杜维尔·基罗斯国际机场

广州白云国际机场
-
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



青岛
-
蚌埠

抚州
-
深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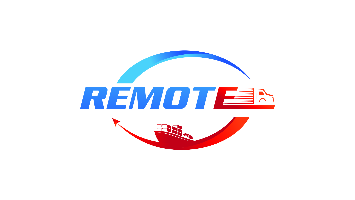
威海
-
广州








